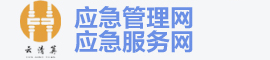
经济人
黄少卿专栏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并且强调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如何解读这些阐述所蕴含的政策取向?依据这些阐述,国有企业下一步改革的方向何在?
其实,“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概念并非首次提出。1999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已经使用了这个概念。作为一项推进了多年的改革议程,国企改革需要的不仅是新思路,也是更大的决心和勇气。
无论下一步将推出什么样的改革措施,笔者以为,它们都需要解决以下几个核心问题:第一,国有资本应该布局在哪些行业和部门,其中保持控制地位的又是哪些?第二,不打算再布局或保持控制地位的领域,应该以什么方式实现国有资本的退出?第三,未来国有资本将以何种方式展开运营?第四,拥有国有资本(股权)的公司,应该如何建立并完善其治理结构?
下一阶段要加快收缩国有资本布局
如何进行国有资本布局,是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也是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早在15年前,如何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就明确指出,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经济要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其他行业和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集中力量,加强重点,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
这样的表述背后是有其学理依据的。当时由陈清泰、吴敬琏主持的“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课题组建议,国有经济应该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而专注于存在市场失灵的公共产品的提供。在一般性竞争领域,国有经济并不能体现出比非国有经济更大的竞争优势。事实上,根据许多学者的经验估算,处于同一行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生产率,要比民营企业的生产率更低。这也意味着,长期来看,如果存在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一般性竞争领域将无国有企业的立足之地。
然而,“有进有退”的国有资本布局调整战略并未得到实现。2006年,当时的国资委负责人对于国有经济应该介入的领域进行了宽泛解读,共有7个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被认为要保持国有经济的绝对控制力,9个重大行业被认为要保持相对控制力,而其中不乏属于一般性竞争领域的行业和部门。从那以后,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基本停滞下来。而且基于这种宽泛解读,以及各种相应的扶持措施,国有企业在不少本应属于竞争性的领域形成了行政性垄断的格局。
国企改革目的是为了做大做强国有经济,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要做大做强所有国有企业,也不意味着国有经济要在所有领域做大做强。下一阶段,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对国有经济布局最低限度的划线:凡不涉及市场失灵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领域,国有经济都不应该介入。相应地,现有配置在这些领域的国有资本都应该退出,转而向应该介入的领域集中,实现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的做大做强。这意味着下一阶段要加快收缩国有经济布局。
依靠法治遏制国资退出中的资产流失
当前,国有资本广泛分布在许多产业和部门,国有经济布局的收缩,必然涉及到国有资本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的问题。理论上,国有资本的退出机制并不复杂,不外乎向个人或非国有的企业法人出售国有资本,包括国有资产整体或部分转让、国有资本或国有股权被收购,以及国有企业被兼并。国有资本的退出和非国有资本的进入相配合,才能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形成与壮大。
问题在于,如何防止国有资本退出过程中发生国有资产流失(严格说应该是国有资本流失)?十多年前,“管理者收购”(M BO )一度成为国有资本退出的主要形式,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国有资本被低价出售的个案。这一现象被有些人成功地利用,来否定、阻击国企改革,导致在相当长时期内国企改革处于停顿状态。然而,改革的停滞并不意味着国有资本不再流失,恰恰相反,部分国企内部人及掌握国企实际控制权的部分官员,趁机挖掘各种“暗道”,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大肆侵吞国有资本。
要重启国企改革,就必须设法遏制国有资本退出时可能发生的国资流失。如何保证国有资本出售价格能够反映其真实的市场价值?为此,政府首先要建立健全公平进入的国有资本转让市场,允许不同所有制主体平等地参与到对国有资本的竞价过程。转让市场既可以是股票市场,也可以是各类产权交易市场,还可以是股权拍卖市场。过去,国有股权的转让定价严重依赖一些评估机构的事前估价,然而,任何国企的资本价值,恐怕很难有人事先能够做出准确评估,而只能依靠企业家们独具慧眼的价值发现。参与到竞价过程的企业家越多,最终的出售价格才越有可能逼近国有资本的真实价值。
要实现国有资本转让市场的有效运行,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法治。法治不但保证每个竞争者平等参与的机会,保证每个参与者的权利---譬如,对拟转让国资企业的信息知晓权、转让程序的公开公正性---不受其他参与者的侵犯。更重要的是,法治能够为全社会公民---国有企业的名义所有者---对国企内部人和掌握实际控制权的相关官员提供一种监督和纠正机制,从而更有效地遏制他们对国有资本的“掠夺之手”。在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改革能否公平有效地推进,实际上是对中国政府法治能力的一个考验。